3月12日,本文初稿呈请台湾烟壶收藏家黄求平先生勘误,先生回复:“不得了,雪村氏一文有好几处会对内画网上资料颠覆,甚至是核弹级的冲击。”
事情缘起黄求平先生的一个存疑。
一
黄先生读了我写的《中国内画的吴建柱》一文,其中节录了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五月,上海交通大学编行《交大季刊》第十三期科学号谢惠《山东博山玻璃工业概况》,“查内画之业发轫于逊清光绪时,是时北平周乐元氏,颇负盛名。周氏故后,冯少轩氏继之。博山有料客王东海者,贩货赴平,因交易而识冯氏,遂得其真传。回博后,授其艺于毕荣九,毕氏又授予张文堂及袁益三(永谦)二氏。(毕氏善山水,张氏则精花卉)今王袁诸人,相继物故,而博山之能内画者,有梁文焕,赵心如,张子祥(山水花卉),辛西园(山水),王如亭(人物),孙雪村,及薛禄万诸氏。”提出里头是不是误植了很多字?像王东海、冯少轩、薛禄万?
我说王东海是不是王凤诰,冯少轩是不是马少宣,薛禄万是不是薛京万,待查证。也不排除作者笔误,编辑失察,造成错讹。黄先生又问,孙雪村你了解吗?顺手发我一幅孙雪村国画《虾》,说这画的年款与年纪都对比得起来。我说,我认为,张雪村先生是鲁派内画先师里头水平更高的一位,但交大季刊所载孙雪村确凿,我与其嫡孙凤鸣相识。黄先生说,证实了,真有其人。
那么,问题来了。黄先生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存有三只早期鲁派内画鼻烟壶,当来自北京故宫。溥仪离开紫禁城是1924年,清宫国宝出北京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一批国宝整理装箱1933年启程南下,后全面抗战爆发,清宫国宝再也没回北京。
陈列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三只鲁派内画壶
这三只鲁派内画壶颠沛流离、辗转多地,最终落籍台北。三只壶的作者分别是雪村氏、辛氏、无名氏。无名氏那只,套料壶坯,显著的博山风格特征。署名雪村氏那一只,落款庚戌年(1910年)。黄求平先生征询是否是孙雪村作品。
台北故宫收藏的孙雪村内画壶
黄先生说,此壶年款为庚戌年,且壶形、画风、壶盖断代为清末。孙雪村内画鼻烟壶从北京徙至台北符合历史背景。黄先生还提供了流落海外的其它几只内画壶,署雪村氏款。查阅孙雪村先生年表资料,不得,旋就教于中国内画艺术大师吴建柱先生。
二
孙雪村先生
吴建柱说,孙雪村与我父亲要好,经常领着大孙子来我家喝豆汁。当年我进博山琉璃合作社,是孙雪村领着去的。那时就知道孙雪村画画很有基础,为琉璃社加工(画)压方条。大炉上拔出的条,三公分左右宽窄,裁断以后两头磨平,背面磨砂,在砂面上画山水,水墨加国画色,晾干,涂上一层白漆,盖住,一回画上几十幅,放进一个篮子,与大孙子凤鸣一前一后抬着,往内画组送,一幅挣两三毛钱。
孙雪村压方条作品
孙雪村琉璃压方条画稿(18×3.4cm)
孙雪村的壶不多,吴建柱没见过。听闻台湾有雪村氏作品,吴建柱说博山有两位雪村,孙氏和张氏。此壶不是孙雪村所作,便是张雪村所作。但屈指一算,张文堂公子张雪村出生于1906年,庚戌年(1910年)仅4岁,几无可能,而孙雪村时年14岁,可能性较大,时人十二三岁即能从事某个职业。壶上有印章,模糊不清,吴建柱认为当时人们在壶上落的穷款,只是意思意思,一点红而已,难以看清。
孙雪村崇拜齐白石。他的画,按年去家里送给吴建柱父亲,博古,白菜,荷花,水墨大写意,灵动,活泛,多使用没骨画法,与内画艺人作品迥然不同。送来的画,都是单片,宣纸也有,硬纸也有,没有装裱,四个图钉一摁,挂到墙上,看个年年数数,墙上潮湿,一年下来已经不成样子,年底打扫屋就扔掉,现在孙雪村的存画还有没有,不好说。孙雪村干卫生所,不喝酒不抽烟,精瘦瘦大高高,细高挑,悠闲时从税务街跑到赵家后门美琉厂内画组和艺人们攀谈攀谈,齐白石咋着咋着,老艺人们听着陌生,也不接受。他说话诙谐风趣,好与大家开个玩笑,曾经说过,你见人是胖子,脖子粗短,一准是血压高,其实先生暮年血压奇高。孙雪村家庭富有,活得滋殷,豁达,为人也好,经常陪着艺人们出去玩,拿着儿子孙启祯的照相机,为大家伙拍照。他们常去的地方有团山,花果山,九龙峪,小顶,在小顶庙里羊肉炖豆腐。人和善,历次运动没受冲击,文革开始不久先生病故。
孙家有个字号叫福成祥,居西冶街,清末时有大炉,老一辈做过烟嘴、烟壶、铺丝,后兼做糕点,到孙雪村时,改营膏丹丸散大药房,类似景泰成,解放后父子两人都进入卫生系统,后在税务街卫生所工作,挂号,儿子孙启祯成为西医大夫。正月十五扮玩,他会糊上两个墙灯,画上荷花菊花,挂到卫生所门口两侧墙上应景。
三
既然吴建柱先生讲孙雪村绘画擅大写意,我想,纸上风格自然会迁延到内画上。我再次拿出孙雪村先生内画图片端详。台北故宫那一只,正面是石头、兰草,兰草肆意挥洒,力道遒劲,倒极似在纸上作画,神似多于形似,是写出来不是画出来的。背面是墨竹,更是率性写意。另一只款识为庚戌仲夏雪村氏的山水壶,国画没骨画法,多施展雨点皴法,意境空蒙,韵味十足。细观孙雪村存世不多的几只烟壶,让人对画面背后的纸上功夫深信不疑,这是与工匠风格的内画家形成显著分野的特质之一。
吴建柱师从张雪村,亦从未见过孙雪村内画作品,然冥冥中却传承了孙雪村写意画风一脉。孙雪村作品藏于北京故宫,后迁徙至台北故宫,而吴建柱内画《田园风味》、内书《李空同诗二首诗》1996年同样为北京故宫收藏,这是鲁派内画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情,更是中国内画艺术史中的一件趣事,在众多内画家谨遵工艺范式绝不逾矩半步的内画界,清晰可见孙雪村、吴建柱开一脉清流,在内画上寻求中国文人画式的表达。孙雪村、吴建柱的努力,均在于试图脱胎鼻烟壶的工艺范畴,向更高层次的艺术范畴靠近。
不管吴建柱先生是不是意识到,是不是认可,我是这么认为的。
北京故宫收藏的吴建柱内画
四
我请教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孝诚先生,对孙雪村先生还有没有印象,先生说,当然有印象,“老先生给美琉加工过压方条,58、59年经常到内画组去玩,为人很和气,对我们这些小徒弟很关心。对老先生的内画没有印象,他的国画是石涛的画风,不随工艺俗套。”这是原话。
张广忠先生对孙雪村印象是画国画也画内画,学齐白石,以荷花居多。1960年左右参加过画展,画的是荷花。
王继泉先生说,孙雪村是美琉孙华章的三爷爷,曾经在聚乐村附近开了个门市,卖些古董字画和工艺品,从玻璃窗往里看,看见有字画,砚台,琉璃和毕荣九及别人的鼻烟壶之类的东西,他自己还临摹过齐白石的虾、螃蟹等绘画作品,他卖过鼻烟壶,但没听老艺人说他会画内画。他高高瘦瘦,很和气,很干练,和老艺人薛京万经常在家庙胡同内画组唠家常,字画并不怎么出众。
李克昌先生也没见过孙雪村的内画,印象中他是一位老师,是位写字的书法家。
张维用先生更不知道孙雪村会画鼻烟壶。
博山文化馆著名画家王烈(1940年6月—)六十年代初学生毕业分配到博山,经常到孙雪村家里学画。上门学画的还有淄博铁路系统国画家王延昌。
五
我又请教王烈先生。先生今年整八十,长期在博山从事美术创作,专攻写竹数十年,被于希宁、王企华等誉为“齐鲁王竹子”。先生接到我的 *** ,高兴不已:
“我对孙雪村很有印象,我给你讲一下,很靠前的事情我不了解,只能说说他跟孙雪村的一段交情。那时他已经是六十来岁了。他儿子叫孙启祯,干医生,在博城医院。我与孙雪村是怎么认识的?我1961年的11月份分配到博山,正好淄博市工人文化宫和博山文化馆搞迎春画展,我就参加这个画展。送了两件作品,一件是源泉二郎山写生画,一件是花鸟画牵牛花。展览是在百货大楼对面香市街口小二层楼上。我去看展览,那天下着小雪,天气很冷,看到三个老头穿着大皮袄,带着棉帽子,也去看展览,走在我头里,我在后头跟着。
“到博山以前我就听人说,淄博有十个老艺人,心心恋恋想,我咋能见着这十个老人,很想着见有个机会见着他们。整好这次有三个老头,看着年龄差不多,就寻思,这三位也许就是那十大老人中的三个吧?
“爬上二楼那个楼梯,进了展室看画,三个老头在头里,我跟在后头,也不做声,就在那里看。看着看着,看见我那个源泉二郎山小寨写生,有个老头就说,这个画画的不是咱这里的人。可能博山经常搞展览,他们对当地的画家都熟。没大见这个画法,就这么说。走着走着,又看见了一幅牵牛花,就说,吆,这两幅作品是一个人画的,这个人也画山水也画花鸟,这不是博山人啊说是,不是博山人画的。也没听说有这个人。另一个老头就说,你猜猜这个人年纪得有多大?也有猜五十多岁的,也有猜四十来岁的三十多岁的,猜年龄的时候我就跟上了,抢先说话了,我说三位老先生你们好,这个牵牛花是我画的,还有前边二郎山那个山水也是我画的,拱手向老者们作了个揖,请三位老者多提宝贵意见!这些老头们摘下老花镜来弓下腰看我,猜的年龄不对啊这个人年轻啊?才二十来岁,都瞪着眼看我,很惊讶。有一个瘦老头就问我,住在哪里现在?我说我住在人民剧场哪里哪里多少号,以后我也没多问他们,就断定他们就是那十位老艺人当中的三位。
“隔了一天的一个下午,有一个胖小孩去找我,也就是十四五岁,愣胖,谁啊?孙雪村的孙子孙大鸣,你是谁啊你又不认得我?俺爷爷叫我来叫你。你爷爷谁啊?俺爷爷是孙雪村啊!你爷爷是不是去看展览来?是啊!好好,我到你家里看看。就到了孙家,一看,是博山西冶街门牌90号。之一次上孙雪村家里,我已经吃过饭了,又吃了煎饼、骨头汤,这是之一次来他家。介绍了他的儿子叫孙启祯,在博城医院,又介绍了那天看展览的另外两个老头,一个是李左泉,一个是李庆章。说李庆章年纪比他们都小,矮的叫李左泉,他和李左泉是表兄弟俩,李左泉是昆仑陶瓷厂,李庆章是山头陶瓷厂,他是在西冶街那个中药铺里挂号,就说我的画不像年轻人画的,问了我家是哪里,我说我是沾化利津的,说了一些。
“以后孙雪村老师还让孩子来叫家去吃饭。这位老者对我挺好,以后还叫我在他那里画了好几张画,画过泰山后石坞的万竹林,画过松树。淄博的厂矿企业歇礼拜六,到了礼拜六老头们都上孙雪村家去玩哩,聚会啊到那里,以后又增加了好几个老者,薛京万,光焰,还有个叫什么章的,刻章的、画画的、写字的都是,都到这里来,其中朱一圭还去了好几回,就像一个小文化圣地一样。他家里好喝茶,抱着个小茶壶喝茶。有兴致的时候,我也看到这些老者画画,画不大,那时候更大的也就三尺,高兴了就画画。老头们有兴趣时喝着茶水,画个画吧!我看过李左泉画过仙鹤,看过李庆章画过仕女人物,看着孙雪村画过虾,荷花。有时候还用毛边纸画。李左泉从那对我也挺好的,我有李左泉好几张画,都糟糟了。看老者们画画,看到他们的一些性格一些习性,也学了不少东西,老头们也讲讲用线啊,用墨啊,中国画的技法讲得不少。还讲到张雪村画雪景,谈的领域很广泛,还谈到李左泉画画的风格,向李左泉求画很难。
1959年淄博瓷厂老艺人与江西陶瓷艺人聚会合影(张明文提供)
“后来就搞开运动了,机关五反四清运动,还牵扯我。我那时候年轻不知道好歹,不大服从领导,领导光给我提意见,光批评我,以后我搬家到了香市街门牌10号二层小楼。62、63年,老头们还去我那里玩,加上了陈佰鸣,画画的场所移到我这里了,也谈篆刻也谈书法也谈画画,就这么些交往的故事。到了64、65年,文化大革命来了以后我就成了博山的头号被批斗者了。那时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亲不亲阶级分。斗我的时候之一条就是,阶级立场不稳,成天和地主资产阶级坐在一条板凳上。大字报上就这么写。为啥和地主资产阶级坐在一条板凳上?就是搬到香市街门牌10号的时候,那些老头们礼拜六都上我那里去。我那里的宣纸随便画画随便写字。外人知不道,光看见一些老头上我那里去,知不道在小楼上鼓捣啥。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资本家还是这个那个。就说我是阶级斗争意识很淡薄,阶级斗争观念不强。
“孙雪村的画画得好啊,比李左泉画得好,李左泉那时候主要临任伯年,写意画画得也快,造型也很准确,笔墨也很酣畅,孙雪村画的题材不多,齐白石的虾,画个荷花,画个南瓜,画个花卉,不大画山水。李庆章就光画仕女人物,但李庆章山水也画得挺好。孙雪村画过内画我听人说过,为啥不谈这一个呢?因为我不了解。”
孙雪村《群虾图》
《群虾图》局部
六
画家王延昌先生(1949年12月—)与孙家近邻,他告诉我,自己从小喜欢绘画,14岁左右的时候,郑家峪李家窑铁木制修厂(后并入博山木器厂)出于往家具上油漆、做漆画的需要,吸收王延昌进厂工作,不料他怕大漆,对大漆过敏,咬着他好几回。又推不出去,改干了木工。
那时候孙雪村在西沟口对面西冶街卫生所挂号。王延昌学画,视孙雪村为启蒙老师,便经常往孙家大院跑,这是西冶街中部偏南坐东朝西的一个大院,与聚乐村斜对门。临街大门进去,下九层台阶,往左一拐,一个大门,便是孙家。进去就是一个大院,三间大北屋,右手一个圈门(月门),进去又是一个院子。孙雪村给王延昌的印象非常深刻,认识的时候,先生年纪大了,每天拄着一根柺棒,挪悠着走步。
王延昌记忆中,孙雪村家中人来人往,高朋满座,他交往人虔诚、忠厚,语言表达从来不得罪人,说话让人感觉很亲切,都是当时博山地面上写字、画画、玩文石盆景的人,每天晚上如此。客人多,孙雪村就得不断劈柴火烧水沏茶,王延昌就利用工作的方便,每个礼拜收拾一箱锯下来的榫台,就是开了榫卯遗弃的下脚料,拿到孙家烧水。大家所谈,不外是远近文史知识,谁谁谁玩过什么东西,写过什么字。经常提及齐白石,怎么画虾米,怎么画白菜,老人画的也比较多,年纪已近七十,仍很勤奋。文玩就说一代文石收藏大家李士儒,把博山文石玩出文化的人,战争年代他与组织往来的鸡毛信,都是大篆、小篆来写,他亲手修建了博山公园的猴子山。孙雪村有个好友,是县前街医院里头的西医大夫丁希堂(音),很有学识,对书法造诣很深,魏碑写得极好,孙雪村里间卧室迎门床头上,正中就贴着丁希堂的魏碑。孙雪村说过家里做过琉璃铺丝,画过铺丝画。与李左泉之间有很深的交流,关系比较密切。王延昌从兵团返回博山,母亲告诉他,你孙大爷跌着了,身体不大好,赶紧去看看。放下行李就跑了去,床上的孙雪村见了王延昌,使劲握手,满眼是泪。孙雪村去世以后,基于他们的深厚感情,孙启祯把父亲使用过的多数印章赠给了王延昌,珍藏数年以后,王延昌又将印章完璧归赵。孙雪村的名章、闲章,有石头的,也有青铜的。
孙雪村先生晚年像
听说我要写写孙雪村,王延昌直说该写:“人家这家人家,在西冶街名声很大,口碑非常好,老先生的儿子孙启祯,当大夫,无论是谁家,晚上几点,家里头出了病人,请孙大夫去看,从不推辞,孙家大门在西冶街上声望很高。日本鬼子进博山前,国民 *** 解散,粮店关张,炉匠与普通市民吃饭无着,抢了西冶街,从北头抢到南头,景泰成也抢了,抢福成祥药房,有人说,抢人家药房做啥,想吃药吗?竟然躲过一劫。”
七
我是与吴建柱、王烈、王延昌等先生聊完,最后才与凤鸣见面的。凤鸣的回忆再次把我带进那个充满欢喜,又不无悲怆的博山家庭。
本文作者与凤鸣
孙家的老街坊南同海曾说,咱们家(指孙家)真是了不起,兵荒马乱时候还收养过两个穷人。这事在凤鸣那里得到验证。有一个叫翠姑,凤鸣说。家是大核桃园进去右手之一个门,为啥收养翠姑?凤鸣说父亲是亲姊妹三个,大姑二姑。大姑上学路上遭遇了坏人,受了惊吓,死于非命,爷爷非常悲伤。翠姑姊妹们多,家境不好,经常饥一顿饿一顿,被孙雪村从小收养来,聊以抚慰丧女之痛,名孙启翠。后来工作到了周村。1961年,孙雪村的老伴去世以后,翠姑在周村听说,跑回孙家大哭了一场。还收养过一个男孩,叫小××,有的话也八十多了,住在凤凰新村。赵增儒的父亲赵玉芳知道博山的事多,曾跟凤鸣说,这个小××,解放前在西冶街南头河滩串悠着要饭,成天脏兮兮,饿得三根筋挑着一个头。有人找到孙雪村,你看这小孩多可怜,弄到你家里,给他一条活路吧!孙雪村就收养下来。多年以后凤鸣每逢见了××,他就是个话痨,摘不下话把子:“我上你家里去时,那个二姑摁住我给我洗头,好没疼煞我。” 小××也许从小就没洗过头。那时候就开着福成祥药房,雇着两个伙计,吴建路,王家来(音)。凤鸣父亲孙启祯从博山县私立进德小学校高小毕业,也在药房,未再进修,后来见同窗间有人当教师,有人当医生,也暗生悔意。小××被收养来,在药房打打零工,家里有活也掺和着干点,生存正经有了眉目。后来才知道小××并非孤儿流浪,有家,家在石门。
孙雪村的晚年并不肃静。
一解放,私人店铺雇佣三人以上就可划为资本家。依福成祥药房规模,放到上海连小业主都不够格,在博山就是资本家,小××竟成了判定孙雪村资本家资格的最后一个筹码。
1952年,孙雪村、孙启祯携福成祥药房加入博山联合诊所,在西冶街小高家胡同,折股金仅一百余元。解放以后,三个伙计各奔东西,吴建路去了建陶,干会计。王家来不详。小××去了水泥厂,也活了一家好人家。赵玉芳以后见了小××就骂,小舅子不懂人活,文革的时候你还诉苦,孙家救了你一命,倒成了剥削,你忘了自家在河滩里时没啥吃、住墙旮旯!诉苦归诉苦,小××见了孙家人还是觉得亲,里外都觉得亲。
孙雪村进联合诊所,先在西冶街卫生所挂号,后在税务街卫生所挂号。孙启祯进了联合诊所,分在西药房。他人聪明,很能学习,喜欢钻研,接触拉丁文之类的外文,赵玉福曾说孙大夫会说三国语言。后在博山商业职工业余红专学校进修完初中,后去市立医院、区中级卫生学校等处进修,1959年转内科临床工作。
孙家解放前两个院子,二十多间住房,解放后还住着十来间,一直是私房,其中三间大北屋是真正的洋房,水泥蘑菇石的外墙,厚厚的黑色泥瓦,叫洋瓦,带厦檐,檐下有灯,屋内是实虚棚,按着吊灯,电灯开关不是拉线,是捹上去捹下来的按钮,捹开这个灯,上一个灯自己就灭。门大窗户也大。带地炉地窨,依过去琉璃大炉埽道而建。室内后墙位置一个下起,建有澡堂,底下有炉子专烧热水。孙凤鸣清晰地记得小时候,大北屋底下的地窨里堆着一堆鼻烟壶壶坯、各色小琉璃花瓶。
八
孙家的女孩出嫁都晚。凤鸣大伯家的大姑很有文化,嫁给了刘同佑父亲刘蓬山,做了填房。亲姑(二姑)让西冶街日升恒赵家说到了济南的亲戚翟姓人家,也给人做了继室。凤鸣小时候还跟着奶奶去济南看过二姑。二姑夫前窝里仨儿,二姑去了又生了俩。二姑父嘴巴随性,说了不兆头的话,被打成右派,极右,关了牛棚。二姑父的大儿媳妇在居委会工作,一看父亲被关,继母带着两个儿子也难,留在跟前是个累赘,就让打发她们娘仨回博山,是在1963年。介绍信上写:转博山人民公社。大表哥与凤鸣同岁,出生在1951年,表哥8月,凤鸣10月。
孙凤鸣翠姑在后院(孙启祯摄)
二姑娘仨回博山那天是个下午,正是凤鸣生日,吃地瓜面菜包。地瓜面刚蒸下来没法吃,发黏,得晾晾才能吃。凤鸣记得大家都在地炉台上吃饭,蒸包搁在盘子里,抓着吃。那几年当紧,没啥吃,凤鸣父亲孙启祯,认识李家窑、掩的、赵庄卫生室的大夫,骑上自行车找人家买点菜,掺和着吃。人们都吃糠咽菜,卖给一点很不容易。
二姑回来娘家,不是长法。孙家挨门有个刘长江,外地人,画画,画人像。时兴唱电影歌曲,刘三姐,马兰花啥的。刘长江画上剧照,抄上歌谱,凤鸣父亲就用相机翻拍下来,洗成五寸照片,叫二姑出摊子卖照片。照片见了太阳就卷,回来再用水泡软,上光,再卖。挣钱了了,一张几分钱。凤鸣从小对摄影感了兴趣,就是自此时。陪着父亲,在屋里挡煞窗户,父亲用暗箱曝光,没有定时器,用嘴数,一、二、三……撂进显影盘,凤鸣就看着显影,成了放到清水里冲冲,定影。父亲又让二姑学照相,拿个120相机,跑岭西、莱芜,给人家照全家福,下步走。照回来洗上,再回去,换点地瓜干回来,将就着维持生活。三张嘴,两个大男孩,当能吃饭。
孙凤鸣姊妹五个,兄弟仨。加上爷爷、父母八口,二姑回来家进来三口,十一口人吃爷爷、父亲的工资。关键是二姑三口人没有粮食定量,从济南回来落户口落不下,没有口粮。说你是博山人民公社,是农业户口,想进赵庄、李家窑人家都不要,农民有点地可以分点菜,分点粮食,进来三口子,地从哪里出?都不要。最后父亲找了北岭生产大队,好歹收下了娘仨。二姑大家闺秀出身,下地干活,别人十分工,她也就挣三分,毛数钱,一直生活困难。十来岁的表弟翟永宁顽皮,夏天跑到李家窑北坡托锁庙水库洗澡,这水库不大,接就一个陡坡砌了一个U型坝蓄水,不了解地形的小孩从坡上下水,一溜就沉到底。翟永宁下去,就没出来。
文革后期二姑父出狱 *** ,来了博山,在西冶街冷家店赁点房子住,后搬到北岭,时间不长二姑父病故。还是赵家,又把二姑介绍到淄川口头弯头村,找了另一个姑父。与凤鸣同在淄博一中上学的表哥翟康宁,听课闹革命的时候,跟着母亲,凤鸣的二姑去了湾头。凤鸣爷爷孙雪村病故前,二姑曾经回博山护理了一段时间。在湾头,二姑夫、二姑相继去世,翟康宁一直生活在那里,一生贫苦。
九
孙雪村腰板直,好挺胸,拄着拐棒挺有气派,早晨四五点就起来,写字画画,出去走哒。凤鸣一直跟着爷爷睡觉,冬天里得让凤鸣蹬着他的 *** ,他则蹬着凤鸣的 *** ,换着暖和脚。1966年冬天,下了雪,早晨走哒完了回家,下九层台阶的时候不慎溜倒,胯骨骨折,一直在后院屋里床上倒着。孙启祯在两个院子之间拉了一根线,这头系上一个铃铛,那边有事,一拉铃铛,这边赶紧去伺候。倒的时间一长就得起来坐坐,刚一坐起来,哎吆使得慌了又得倒下。倒的时间长了,大便干结,孙启祯就拿铁丝做个钩子,在父亲 *** 上往外抠。弥留的时候,有次屙在床上,拿手指头沾着秽物,在墙上画了一个金鱼,极完整生动。没有多久,有个晚上,眼看老先生实在不行了,一家人围在跟前,孙启祯拿着听诊器,按在老先生心口,听着老人渐渐没了心跳。
1990年,西冶街拆迁改造,第二百货公司盖商场,贴着孙家大院北墙,三四层高,孙家大院一览无余。再扩建锅炉房,占了两个院子,十几间房屋、一眼井,加地面附属物,作价计一万余元,孙启祯爷俩搬到了峨眉新村公房,不久即房改,掏钱再买下来,想想就得冤煞。
十
写到这里,忽然意识到释然了一个大大的疑惑——孙雪村内画作品何以存世稀少?当代资深内画大家何以多数不知道孙雪村画过内画?有三点发现:
其一,孙雪村家境富裕,自清代以来开琉璃大炉、有料货庄、大药房,素无缺衣少食之虞,少年既有绘画天赋,却无须以内画糊口,故不需以内画为业,换取米粮,自然不会大量绘制内画,只是兴致所至,遣以兴致;
其二,雪村暮年,命途多舛,心力腕力渐失,眼色更有不及,怕是再也不愿拿起内画勾笔;
其三,孙雪村擅长泼墨写意,有强烈的文人情趣,潜意识里排斥匠气,不屑被一只小小琉璃瓶所束缚,偶有把玩,也只是一时雅兴而已。
这便是后续内画传人鲜有知道孙雪村画过内画的原因。
一份博山区书画历史名人资料上记载,孙雪村(1896年—1967年)以字行,名兆瑞,博山西冶街人,自幼业儒,稍长从事琉璃内画。1934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季刊》博山琉璃考察史略载:博山内画名人有毕荣九、张文堂、袁益三、梁文焕、赵心如、张子祥、辛西园、王如亭、孙雪村、薛禄万共十人。先生爱好收藏,尤工于画,以大写意花鸟为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曾任职于淄博市群众艺术馆,教授国画技法,学者多有成名。
再度细查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五月上海交通大学编行《交大季刊》第十三期科学号谢惠《山东博山玻璃工业概况·内画史略及 *** 》,知道该文系作者谢惠任教济南时携学生六人对博山玻璃做数度调查所得,其中载有:
“博山四周,平原稀少,崇山峻岭,故矿产之富,甲于他邑。煤炭而外,尤多玻璃及陶瓷之原料。二百余年前,该处玻璃事业已极发达。颜色如蓝,绿,映青,牙白,正黑,秋黄,鹅黄,梅萼红等,无不具备。清乾隆以后,相传一男人到博,发明一种红色,名为金红,更为美丽。惜秘不传人,故至今能制成者,全城仅义太永一炉而已。又如洋青(即钴蓝色),系三十年前刘绪顺氏(应为已故玻璃窑炉专家刘同佑先生祖父,笔者注)无意中由青岛友人处携回洋青一包,试用于料器而传出。至鸡肝色,由当时误用铁末而得之,□(石旁,几何的几繁体,或为珊之误)瑚色料器则由日本输入之料条制成,博山尚不能仿制……料货分为数种:有带色者,有水晶者,大至花瓶,小至鼻烟壶,无不精绘花卉人物,初见时或疑为印就,实则为人工绘成者,因其画均在内面,故名之曰‘内画’。查内画之业发轫于逊清光绪时,是时北平周乐元氏,颇负盛名。周氏故后,冯少轩氏继之。博山有料客王东海者,贩货赴平,因交易而识冯氏,遂得其真传。回博后,授其艺于毕荣九,毕氏又授予张文堂及袁益三(永谦)二氏。(毕氏善山水,张氏则精花卉)今王袁诸人,相继物故,而博山之能内画者,有梁文焕,赵心如,张子祥(山水花卉),辛西园(山水),王如亭(人物),孙雪村,及薛禄万诸氏。然大都直接或间接得之于毕氏也……历来名手所绘之鼻烟壶,以周乐元氏为最贵,现在每个可值数百金,冯王二氏,亦须一二百元。毕氏以下,则数十元至三五元不等,内画之贵,可见一斑矣。”
上海交大季刊影印件
十一
如果台北故宫的雪村氏内画壶坐实为孙雪村作品,对现有网上传闻的确是个颠覆,这是黄求平先生的感受。张维用先生《山东博山的早期内画艺人》中引述香港鼻烟壶收藏协会首任会长、著名收藏鉴赏家梁知行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内画鼻烟壶新貌》中语:“毕氏(毕荣九)几个弟子以最幼的张文堂之子张敦瑞(笔名雪村)成就更大。台北故宫博物馆即有雪村氏的作品。”兴许也要打一个问号。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五月上海交通大学编行《交大季刊》第十三期《山东博山玻璃工业概况·内画史略及 *** 》还记载了内画技法:“至其绘画 *** ,甚为离奇。先将铁砂及水,灌入瓶中,用力摇荡,使之内部粗糙,然后洗净待干,以竹制勾条(其形如「)蘸墨,自瓶口探入内部绘之,以瓶质透明,可于瓶之外部见之,绘成之后,再以勾尖裹笔毛,依次着色。内画之瓶,其价昂贵,即以此故。”
十二
截稿当日,收到凤鸣信息,是刘连贵先生在他的《仰石·品茗畅谈石道》里,侧面记载了一段孙雪村的生活雅趣:“孙老先生是开料货庄的。料货庄主要经营博山琉璃工艺品,如花球、杖子嘴、佛珠、米珠、料兽等。孙老先生往返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可谓见多识广。老先生也养成了南方吃早茶的习惯,早上叫伙计们沏上茶水,恣吟地喝上几杯,边喝茶边做生意。孙老先生对茶文化有独到之处,他赏玩的一把宜兴紫砂壶珍藏了多年,包浆浓郁、雅韵隽永。老先生对这把壶十分珍爱,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不仅如此,老先生还有意将这把名壶里装满黄豆并加水浸泡,用麻线绑在壶的外侧,等黄豆发芽后,壶的外表逐渐有了裂纹,但不能过分大了,要达到既有裂纹又不能漏水的程度。然后用金刚钻打孔,用银子锔起来,鲜核桃擦光,每天拿在手里抚摸,时间长了就生出了一层厚厚的包浆,真是颇为有趣。这把壶沏出的茶水散发着淡雅的光芒,给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感,仿佛这把紫砂有了灵性,报答主人的泡养之情。”
孙雪村收 *** 国松石绿琉璃瓶
孙雪村收 *** 国雅石
孙雪村先生收藏的民国钴蓝琉璃瓶
孙雪村用过的画笔
孙雪村生前用过的象牙筷
孙雪村把玩过的民国水仙盆
凤鸣又补录道:“我小时候,爷爷正月十五喜欢扎花灯,五星,扇面,六棱的,画上些国画,他喜欢的鱼、虾米、荷花。有一年,卖酱油醋和水产的友好门市部搬家到了西冶街南头西沟沟口,让爷爷糊了两条大鱼,画好了,来人拿鱼,给爷爷送了两条咸白鳞鱼。爷爷还会扎风筝,给我扎了一只‘呜嘤哇’,两只眼睛会动,我们一帮小孩跑到西圩外头去放,放得挺高挺高,结果断了线跑了,一直跑到大辛庄一耷拉,咋也没找着。那个糊虚棚系秫秸的死扣,你也会的那个,就是我跟爷爷学的。搁伙着老头们上山弄石头,弄回来把纳鞋底的针绑在筷子上剔,拾掇。出去逮促蛰,斗促蛰,一直逮到大昆仑,还误闯了一个军事仓库,人家还不让了。也玩咬乖,冬天满屋子咬乖叫。爷爷玩水仙是一绝,每年玩俩,他玩的和别人不一样,割了栽成蟹爪式。很多人去找他问咋着割,我也就会割了。就是把水仙花头去个四分之一,叶子豁一块去,杆子蹿得也不长,叶子出来就是卷曲的蟹爪式,造型很好看!”
嗬,西冶街上不但藏着一位内画先师,还藏着一位王世襄嘛!这时我才意识到,凤鸣屋的窗台上,春阳刺眼,正有咬乖叫得欢呢!还是两只。
(文中烟壶图片除署名外均为黄求平先生提供)
2020年3月15日青龙居
本文为刘培国先生原创文字
若需转载请联系此公众号
未经授权转载者
将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
转发时切勿删除版权信息
刘培国
淄博世纪英才外语学校执行董事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黄焖甲鱼的做法详细步骤 1、将甲鱼、鸡分别宰杀洗净。放入锅内,加水2500克,葱、姜、八角、旺火烧沸后,改用小火煨至熟捞出。拆肉剔骨,将肉切成2厘米宽5厘米长的条。 2、炒锅烧热,下花椒油、姜、葱丝炒成黄色,放入酱油
品鉴 | 中国传统工艺:传承匠心 惊艳世人来源:文旅中国
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传统手工艺品历史悠久、门类众多、各具特色,不仅反映了历代手工艺者高超的技艺,也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智慧和文化信息。古往今来,许多兼具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手工艺品,或深受文人雅士青睐,或为百姓“日用而不觉”,传承至今,仍然被人们使用、欣赏、收藏。尤其很多传统手工艺品,经由当代传承者的创新设计,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焕发新的光彩、发挥独特作用,甚至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本文与大家共同领略一些汇集众多技艺、文化气息浓厚的中国传统工艺品的风采。
▲ 黄卓 绘
大俗大雅一柄扇
赵润田
扇子,大俗大雅,占尽了这两头。
先说“俗”。空调普及之前,谁没使过扇子呢?甭管是城里还是乡下,三伏天里,人手一把,驱赶着暑热。最痛快的就是拿个大蒲扇,呼啦啦地扇。蒲扇这东西,没什么美感,但实用。街上的老人走累了,把蒲扇往砖台上一垫就能坐下歇会儿。有时也不是为了解热,而是赶蚊子。对脾气的老几位凑到一起,说着话,有一搭没一搭的,最是人间滋味。蒲扇那么可心,简直是个多用途工具,路上遇到雨,蒲扇还可以顶个雨伞,往头上一遮,跑吧。
蒲扇又是个有佛缘的物件,电视剧《济公》里的济公和尚什么时候手里都拿着把蒲扇,这蒲扇破得没法看,却恰合济公的风度。鲁迅画过“活无常”,画面上怪怪的无常手里擎着的就是一柄破蒲扇,裂着大口子,那蒲扇直指前方,是整幅画的力度之所在。
不过,文学作品里很少说到蒲扇——它太平实了,书中常提到的是宫扇、折扇。所谓“轻罗小扇扑流萤”,指的就是宫扇。宫扇也称团扇,都是薄纱所制,上面淡淡地绘一枝花,梅也罢,桃也罢,雅致得很。扇形或圆或方,或细腰葫芦状,就像《西游记》里火焰山罗刹女手持的宝扇那样。宫扇的形制有很大发挥空间,在圆形或方形基础上做出一些细微调整,就有了更为细腻的个性。而且,还可以在扇面上绣花,更好是苏绣,看着就舒服。
唐代诗人有不少题咏扇子的诗歌。刘禹锡写过一首《团扇歌》:“团扇复团扇,奉君清暑殿。秋风入庭树,从此不相见。”他的另一首诗则以扇相喻,说人情冷暖:“莫道恩情无重来,人间荣谢递相催。当时初入君怀抱,岂念寒炉有死灰?”司空图所题也有情有义:“珍重逢秋莫弃捐,依依只仰故人怜。有时池上遮残日,承得霜林几个蝉。”禅林的皎然和尚也咏道:“他时画出白团扇,乞取天台一片云。”可谓联想丰富,气韵高古。
到宋代,团扇依然流行,苏轼、陆游等人都有咏团扇的作品。陆游总不离文人气味:“护砚小屏山缥缈,摇风团扇月婵娟。”“团扇兴来闲弄笔,寒泉漱罢独焚香。”范成大则惆怅得像化不开的雾了:“去年团扇题诗处,依旧疏帘细雨中。”还是南唐后主李煜说得轻松些:“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
▲ 苏绣宫扇 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
现在的宫扇是一种旅游工艺品,游客觉得好看,买回去把玩或是赠人,都是有趣的。但那些禁不起细看的“大路货”更好别买,去看看近年来拍卖场上的老苏绣宫扇,就知道啥是好东西了。
竹扇是自古至今都有的扇子。把竹片削为薄薄的竹篾,纵横相交,外勒以边,镶上竹柄,就成了竹扇。竹扇比蒲扇灵便,比团扇结实,很实用。唐代张祜有首《福州白竹扇子》说得很细致:“藤缕雪光缠柄滑,篾铺银薄露花轻。清风坐向罗衫起,明月看从玉手生。”
羽毛扇当然也是扇中名品,“摇羽毛扇的”甚至成为军师、谋士、帮闲的代称,其中更大的“腕儿”当然是诸葛亮。其实何止诸葛亮,“羽扇纶巾”本来是说周瑜的。白居易有首诗专咏白羽扇:“素是自然色,圆因裁制功。飒如松起籁,飘似鹤翻空。盛夏不销雪,终年无尽风。”
但要说方便而不失雅致,则非折扇莫属。折扇,竹木为骨,素纸为面,可以很简单,到此为止;可以很讲究,精雕细作。明代《万历野获编》说,折扇为“怀袖雅物”。扇子到了折扇这里,横生出无限空间,虽为微物,气象万千,为文人画的随意挥洒创造了一片天地。经由文士、画家的参与,折扇成为表情达意的手段,至少在明清时期,它已成为承载着万千情意的文玩雅物。
清代文学巨著《红楼梦》里多处写到扇子,甚至成为精彩情节。第31回“晴雯撕扇”写豪门主仆听扇面断裂的声音,晴雯解气,宝玉叫好。第48回则借平儿的辣嘴,骂出一段关于扇子的生死案子:贾琏想要得到石呆子的20把旧扇子,但那石呆子宁愿饿死冻死也不卖。《红楼梦》虽是小说,但透露的社会习俗是真实的,我们从中也可得知清代达官贵人收藏旧扇子的风气。
▲ 各式折扇 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
折扇的起源在学界有争议,有观点认为它是宋朝时从日本传进我国的,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其为中国原创,南北朝时期已有折扇,是见于史书的——《南齐书·刘祥传》载:“司徒禇渊入朝,以腰扇障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资治通鉴》卷135齐高帝建元二年“渊入朝以腰扇障日”元胡三省注:“腰扇佩之于腰,今谓之折叠扇。”有人则将两种观点折中,说折扇原出中土,但一直粗糙简陋,传到日本、高丽后被精致化了,在宋朝时又作为贡品返回中土,有泥金面、乌竹骨等多种样子,遂流行开来。
折扇,最紧要处就是扇骨和扇面。扇骨通常为竹质,普通竹子只能做普通扇子,上等扇子必得湘竹、玉竹等。湘竹亦称斑竹,天然有花斑,好看;玉竹竹质细腻,便于雕刻,是刻竹的上好材料。此外,还有紫竹、罗汉竹等稀见种类。至于扇面,无论写上字还是绘上画,都增添了趣味,极具风雅。
几十年前空调未普及时,夏日是折扇争奇斗艳的天下。不少人很在意手中的折扇,它是自己的另一种脸面,展开扇子,就等于展开一个人的文化家当。
折扇的讲究首先在刻竹上。带有刻竹的折扇,曾是上流社会的必要“装备”之一,政界高官、商界大亨、伶界名角、学界文士,无不精心配备,既为自娱,也为与人交际时显示自己的文化品位。民国时北京更好的刻竹者首推张志鱼,张志鱼刻竹在当时号称“琉璃厂三绝”之一,另两绝是张寿丞刻铜、朱友麟刻瓷。张志鱼工篆刻、善书法、能绘画,尤以刻竹独擅艺界,被誉为“北方刻竹之一人”,拥有一柄张志鱼刻竹折扇,足为人前夸耀。
刻竹一艺,有阳刻、阴刻、青皮、沙地等多种形式,其中,画稿是非常重要的。当年张志鱼所刻,多为张大千、齐白石等一时名彦在扇骨上绘得的底稿,然后奏刀而就,原画神采不但全局毕呈,而且还能以刀补笔,做出适当调整,成为一种令人叫绝的艺术品。现在寻到张志鱼手刻已经很不容易了,我曾见过他当年的不少扇骨拓片,非常精妙。
除了扇骨上的雕刻,扇面上的绘画更容易吸引人,许多知名书画家都曾做过扇画,当然,随着价钱越来越高,这些扇子已不再是实用品,而成为极具艺术含量的收藏品了。民国时,请名画家画一幅扇面,索价相当于一平尺,现在则远高于此。如果是一面绘画、一面书法,形成双璧之美,价值更要翻倍。近年来的拍卖会上,成扇是很重要的一类拍品,甚至还有专场。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藏扇,以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为多。
▲ 象牙折扇 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
还有一些扇子,虽然是扇子的模样,但天生就不是让人拿来纳凉的,它们的材质包括象牙、珐琅等,常常是陈设于室内,用于装饰。象牙宫扇、满工花纹扇,那真是工艺绝品。紫檀镶银丝宫扇、象牙丝编织图画珐琅柄宫扇,用极细的银丝、象牙丝编织而成,嵌有玉石百宝组成的花卉禽鸟,套用好几种工艺,让人屏息端详,惊为天物。还有珐琅工艺制成的折扇,取其样貌,实不可开合,安置于木架上作为摆设。这些东西离生活较远,聊备一格,在拍卖会上、博物馆里欣赏下也就够了。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明清时期的文房水盂
“象生”百态
高 塽
▲ 清代水晶兔式盂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水盂,又名“水丞”“水中丞”,是用于存储研墨用水的文房用具。盂这种器型,可追溯至史前,历经数千年的发展,随政治、经济、生活的变迁而发展出多种功能,且遍布皇室礼仪、日常生活、宗教供奉等诸多领域。文房水盂脱胎于“盂”家族,应笔墨书写需要而生,萌芽于西汉,经历了魏晋、隋唐的发展期,至宋代迎来繁荣。明清时期,人们对水盂十分喜爱,各种对水盂的品评见诸文人笔记之中,甚至清代帝王也曾参与宫中水盂的样式设计。明清时期,宫廷的文房水盂一改唐宋时单色釉盛行的特点,各种釉上与釉下彩绘瓷成为瓷质水盂的主流,紫砂、玉、水晶、玛瑙、珐琅、玻璃、竹根等各种材料也被用来 *** 水盂。造型方面,除了传统的盂形,还流行具有各种吉祥寓意的象生形水盂以及与笔架、笔舔等文具融合型水盂。
▲ 清中期德化窑白釉蟹形水盂 英国V&A博物馆收藏
模仿动植物等造型的象生形文房水盂是此时尤具特色的一类,除了储水研墨的实用功能,更以其奇巧造型成为文人墨客书房陈设、案头赏玩不可或缺之物。其实,象生形水盂的出现可追溯至魏晋,比如越窑青瓷中就流行蟾形和兔形水盂。唐宋时期,象生形水盂并不多见,直到明清,各种模仿动植物造型的水盂被大量 *** 。此时的象生形水盂,已摆脱了在扁圆腹造型的基础上贴塑动物头部及四肢的样式,向着更加写实的方向发展,不仅造型更加别致、多样,还附加各种美好寓意。
▲ 清康熙景德镇窑素三彩鼠形水盂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
明清时期,动物造型的水盂十分丰富,大多寄托着多福、多寿、多子的美好愿望。比如,当时出现了不少鼠与葡萄结合的造型,表示多子多福。在海外博物馆可看到一些清康熙年间的景德镇窑素三彩鼠形水盂,为康熙时期特有的彩绘瓷品种,色彩淡雅,十分珍贵。又如,水鸟造型的盂流行于明清时期,被称为凫式盂。凫是野鸭等水鸟的统称,谐音“福”,以此命名,寓意吉祥。以螃蟹作为水盂造型,则因其具有科举得中的美好寓意。《明史·选举志》称:“会试之一为会元,二甲之一为传胪。”因此,世人就以两只螃蟹衔芦苇来寓意“二甲传胪”。蟹形水盂可见德化窑白釉烧造,整体模塑为螃蟹形,左蟹钳夹一银锭,背甲开椭圆形口。
▲ 清康熙画珐琅荷花形水盂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 清中期青白玉菊花式水盂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植物造型的水盂也是多种多样。比如很多花卉优雅美丽,本身就极具装饰性。荷花作为水盂的造型,可为一片花瓣,也可为圆形的整个花朵,各有意境,呈现不同效果。清代宫廷的画珐琅荷花形水盂,口沿下一周绘绿色莲子,再用深浅不同的红色釉料描绘花瓣,浓红艳绿,尽显宫廷华丽风范。菊花是“花中四君子”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被赋予吉祥、长寿之寓意。清宫旧藏中有以玉雕成的菊花形水盂,主体雕刻为一朵团拢的菊花,器壁浮雕层叠的花瓣,外壁透雕曼妙的枝叶,既是装饰又可做执柄,设计感强烈,体现了清中期宫廷玉雕的审美。
▲ 清代白玉葫芦型水盂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 清代玛瑙瓜形水盂 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
除了花卉,瓜果的形状也十分适合水盂。葫芦谐音“福禄”,明清时期宫廷玉雕中可见各式葫芦形水盂,辅以蝙蝠、藤蔓装饰,寓意福寿绵长;瓢形盂,可见于紫砂器、鳝鱼黄釉陶瓷器制品,颜色上写实逼真,追求匏器自然的质感。与葫芦同属一科的瓜类,也常见于水盂造型。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玛瑙瓜形水盂,利用玛瑙自身丰富的色彩施以巧作,器盖以绿色玛瑙圆雕成叶,器身圆雕黄色小瓜,内空可盛水。桃子作为长寿的象征,是表达祝寿寓意时最常用的题材之一。桃与蝙蝠、灵芝等搭配组合,寓意福寿双全、灵仙祝寿等。明清时期的桃形水盂材质丰富多样,有玉、瓷、紫砂、玻璃、竹雕等。雍正时期的画珐琅桃形水盂,盂身呈双桃形,桃尖涂染粉红色,渐变且有斑点,桃实上的绿色也是深浅不同,栩栩如生,令人垂涎欲滴。紫砂桃形水盂,常将底足做成桂圆、莲子、枣、花生等干果形状,贴塑于盂下,寓意早生贵子。
▲ 元代景德镇窑青白釉太白醉酒水盂 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收藏
动植物造型之外,还有人物造型、器物造型的水盂。人形水盂,通常是在水盂一边塑人形,构成一个生活场景或历史典故。“太白醉酒”是水盂造型常见的题材,以此表现文人豁达自信、桀骜不驯的风骨。类似水盂通常为酒缸形状,旁边或塑或雕一个瘫坐斜倚酒缸的人,表现醉酒的状态,人物一般头戴软角幞头,身着圆领袍衫,为典型的唐代人装束。
▲ 清乾隆景德镇窑白釉龙蝠纹水盂 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
仿器物造型的水盂,一般仿的是竹篓、书卷等各种日用器物。明清时期流行包袱造型的水盂,因为包袱谐音“包福”。景德镇窑白釉龙蝠纹包袱形水盂,整体施白釉,口部贴塑蝙蝠和螭龙,二者昂首相望、张口呼应,栩栩如生,寄托“福寿双全”的美好寓意。
明清时期丰富多彩的象生类水盂,既有实用功能,又可把玩欣赏,成为当时文人书桌上一道别致的风景。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扬州画舫录卷十七·工段营造录》载:“几上多古砚、玉尺、玉如意、古人字画、卷子、聚头扇、古骨朵、剔红蔗葭、蒸饼、河西三撞两撞漆合。瓷水盂,极尽窑色,体质丰厚。”可见,当时厅堂之内、书房案几上流行的陈设物品,水盂位列其中。
(作者系北京艺术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内画鼻烟壶
方寸之间观天地
周 隼
▲ 1816年甘烜文内画鼻烟壶 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收藏
鼻烟壶是承装鼻烟的容器,小巧精致,便于携带。明末清初,鼻烟自欧洲传入中国,鼻烟盒渐渐东方化,产生了鼻烟壶。如今,虽然人们不再嗜用鼻烟,鼻烟壶却作为精美的工艺品流传下来。在品类众多、绚丽多姿的鼻烟壶家族中,内画鼻烟壶将中国独特的造型艺术与传统的书画艺术巧妙融为一体,时至今日仍深受世界各地收藏家的青睐。
内画鼻烟壶一般选用玻璃、水晶、浅色玛瑙、金珀等透明或半透明的材质 *** ,壶体通常为扁平,以便有两个平面作画。 *** 时,首先在器物内装入铁砂、金刚砂和水,通过晃动进行撞击摩擦,使壶的内壁呈磨砂状,不再光滑,然后用一种特制的小勾笔,蘸上水墨等颜料从壶口伸入,在壶内反向作画。原则上各种绘画 *** 都可以使用,但一般都是中国画。为适应各种欣赏习惯,现在也有在内画壶中绘制油画的。
据香港鼻烟壶研究者梁知行考证,内画鼻烟壶最早应出现于清嘉庆年间,是由中国南方的一位年轻画家甘桓发明的(见梁知行《中国内画鼻烟壶新貌》)。又据许漠士考证,甘桓的真名叫甘桓文,他创作的内画鼻烟壶题材很广泛,敷色以墨色为主,以淡素的颜色为衬,早期作品是以甘桓署名的,后来也有以甘桓文、一如居士、半山、云峯、古开樵等署名的。现存甘桓文最早的作品是其于清嘉庆丙子年(1816年)所作,一面绘有山水,另一面书写诗文,构图、画技和书法功力均不凡,说明作者绝非初学乍练,已进入成熟阶段。
在大方向确定后,各种流派和风格的内画壶大师以及作品便自皇宫至民间不断涌现。内画的题材也从简单的装饰图案,慢慢发展到山水、人物、花鸟,进而在图画中插入具有故事情节的传说和神话。随着绘画技艺的日趋成熟,又进一步借鉴国画艺术,给每幅作品加上题款、印章,使得内画壶越来越具有欣赏性。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的书法与绘画移植于内画壶,让这一地道的“舶来品”满载中国艺术元素走上国际舞台,成为国与国之间交往时的珍贵礼物。
内画鼻烟壶 *** 技艺主要流传在北京、河北、山东、广东,形成了“京派”“冀派”“鲁派”“粤派”等流派。北京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都,也是内画鼻烟壶的发祥地,这里百业兴旺,人才咸集,经济文化发达,孕育出内画鼻烟壶艺术有其必然性。画工们汲取京城深厚的文化底蕴,逐渐形成诗书画印并茂的京派艺术风格。京派艺人用竹笔、柳木笔作画,以画面厚朴、古雅见长。生于光绪元年(1875年)的叶派内画创始人叶仲三是京派代表人物,他与周乐元、马少宣、丁二仲合称“京派内画四大名家”。鲁派画工云集地在山东博山,鲁派因山东博山籍内画师毕九荣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从北京回到博山后发展起来。鲁派内画用毫毛笔作画,以画面纤巧、艳丽取胜。
鉴赏内画鼻烟壶,除了考量它的书法绘画技艺,其本身的造型也是重要部分。画师会依据每一款壶的造型决定描绘内容、表达手法、题款印章等,更富于文化素养的匠师不再描摹名人字画,而是拿出原创性的书画作品,以奠定自己在这一领域的地位,文人书画中的布局谋篇、意境笔法最终成就了内画鼻烟壶这一综合艺术。从最初高雅的文人画到后来的世俗画、肖像画,内画鼻烟壶在方寸世界中展示着广阔的文化情怀。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2023年8月22日《中国文化报》
第8版刊发特别报道
《大俗大雅一柄扇》、
《明清时期的文房水盂 “象生”百态 》、
《内画鼻烟壶 方寸之间观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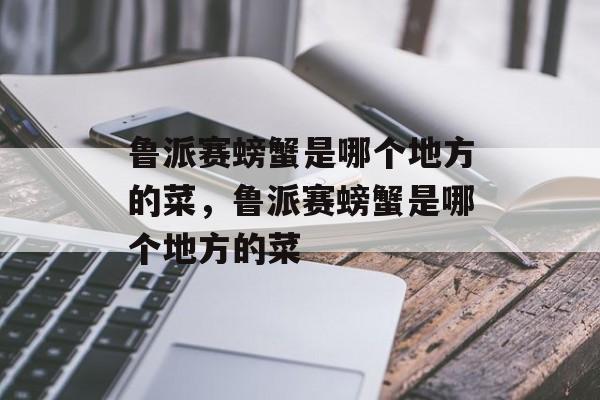
↓ ↓ ↓ ↓ ↓ ↓ ↓ ↓ ↓
责编:陈陈







